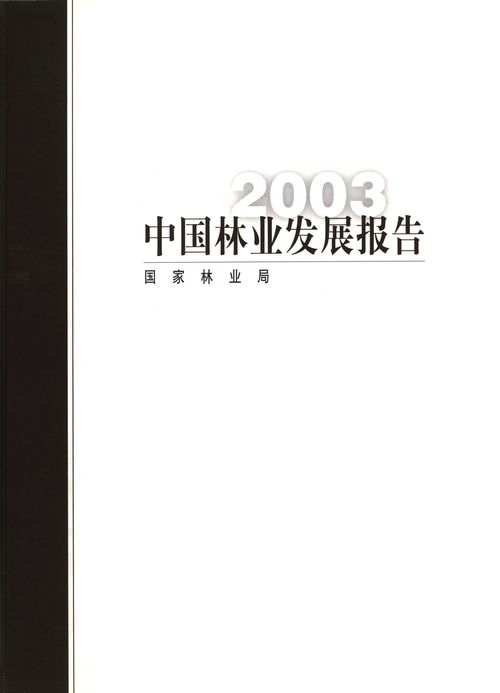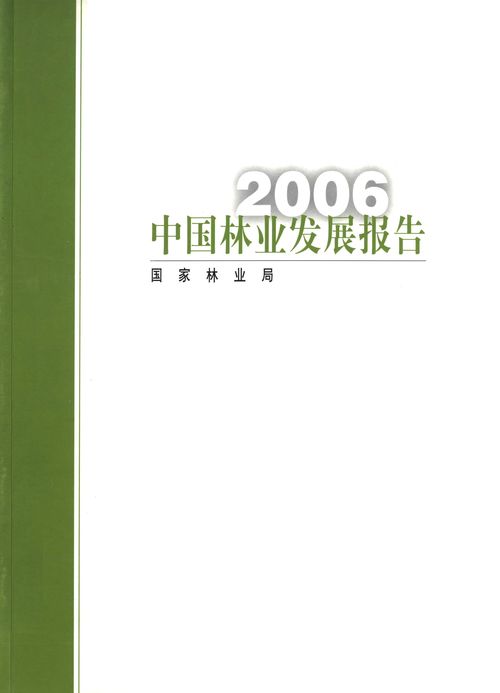陆川谈《可可西里》:一次燃烧内心的拍摄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陆川之飞跃何止千里!”——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陆川
10月1日,陆川新作《可可西里》将与王家卫《2046》同期上映。
这样的选择,本身已经说明很多——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导演的信心和雄心。
另一个让我们关注陆川的因素是,《可可西里》未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不少电影人为之可惜。
从第一部和姜文合作的作品《寻枪》开始,陆川,这个33岁的年轻导演,就注定不能被人忽视。
人物小传
陆川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1995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2001年自编自导电影《寻枪》,参展威尼斯电影节“逆流而上”单元,获2002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
《可可西里》落选威尼斯,可能是因为它并非评委想像中的典型的中国电影。
晶报:曾经有记者在采访贾樟柯时提起你不服气威尼斯的选片结果,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澄清的?此外,对《可可西里》落选威尼斯你怎么看?
陆川:我没有接受过那个记者的采访,我从来不回避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样无端挑拨的做法不光明磊落。我们已经和这个记者交涉过了,他向我们道了歉。我们做电影不是为了电影节做的,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他肯定希望能在一个专业的电影节上得到认同,而且这也是个让电影在更大范围被认可的机会,说不重视是假的。我们太热爱它了,这是我们的孩子,希望它得到一切关爱。但我不会因为电影节改变我的拍戏方式和见解,可能有一种见解是不太容易被国际电影节认同的,但这是我的方式,我还是会坚持。我希望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能作为堂堂正正的电影出现。就这次威尼斯而言,《可可西里》可能未必是他们想像中的、比较典型的中国电影。这和它的眼光有关,和我们电影的质量无关。
晶报:看过顾长卫的《孔雀》么?本来也说要送威尼斯的。
陆川:看过,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剧本,很平静、很庄重,很有力量。虽然它和我的电影完全不一样,但看了他的影片,我挺自豪,我觉得我真的是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间,有一个伟大的战友。
《可可西里》有贴近生命核心的力量。
晶报:关于电影故事,现在流传着很多版本,真实的是什么样的?
陆川:故事还不能说,和原先传出去的版本已经差别很大。它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电影,不是所谓的记录片,只是有真实感,从一个记者的视点拍的。最简单说,它就是讲一次生命历险的影片。八个人三辆车开入死亡无人区,两三个人活下来的故事。在途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然后队员不断地失散,不断地死去,它是一个旅程式的电影。
晶报:你当初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
陆川:就是这个题材打动了我。就觉得里面生命的感受特别强烈,特别质朴。直截了当,就是生和死。其实也没想传递什么,因为我们拍片子不是想给谁上一课,这意思不大,我们只想拍一些能让自己燃烧、让自己激动的东西。制作剧本时,我们就逐渐在接近题材中那种最贴近生命核心、生命根源的力量,最终我们发现这种力量在拍摄过程中,通过我们自身的磨砺、120多天高原的、流浪式的拍摄慢慢地显现出来。
我们在拍一帮普通人,他们用平静展示不屈。
晶报:这样一部电影会用什么样的音乐?
陆川:捞仔写的,很好,很有静气,用非常现代的眼光看待传统,且不卖弄民俗。我觉得这电影最不能犯的两个错误,就是卖弄民俗和卖弄伪英雄主义。
晶报:你说到伪英雄主义,难道影片讲英雄主义么?
陆川:这电影你给它规定任何主义,我都不同意。我们在写一帮普通人,但他们真得很牛。他们的牛是因为他们面对肉体巨大痛苦和险恶生存环境的平静,但却昭示了一种对无奈的不屈。这种无奈中用平静来展示的不屈,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生存、繁衍和创造奇迹的根本动力。我们喝酒的时候经常痛哭流涕,可平常,我们话都很少。不是麻木,是情感隐藏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连起码的改善希望都没有,但他们依然平静地生活着,信仰很多东西。比如善,在他们内心里特别执着。我真的不想写英雄主义,你要是弄英雄主义,那这片子就毁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开阔了,平静了。这片子就有了它应该有的力量。
拍这部戏已经让我成功地由一个青年人变成了中年秃头男士。
晶报:记得有一次电话采访你,你说拍这部戏已经让你成功地由一个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
陆川:中年秃头男士。
很难想像还有第二支队伍在这样一个地区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拍摄。其中有一场戏,我们计划两天拍完,实际上七天还没有拍完。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干一会儿就必须歇一会儿,而且那地方风雪交加,天气一天四变,一会风一会雪一会雨一会雹子一会晴,根本就没法拍,我们就只好等待……经常两天的戏拍了七天,这戏就是这么拖下来的。
晶报:所以就有人罢工,也有些人突然间就不干了。
陆川:其实我不太愿意谈这些事。离开的,的确有,钱都不要就离开了。因为太苦。我也能理解,对有些人,那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你不能要求他像你一样把这片子当作品来做。人家没必要为了他正常的、一个上下班的工作去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没法告诉你那时候拍摄有多么绝望,连我自己都有,计划每天列出来都完成不了,天灾人祸每天不断。你越拍越绝望,人的体力是极度透支。现在看片子,我都在想,天啊,怎么拍的?!那种暴风雪,人站在那儿,上半身是若隐若现,下半身根本看不到的。那种风雪的密度,能见度非常非常低。
如果说拉一条船靠一百个纤夫的话,位置上我可能是排第一个,但我考虑更多的是方向,而不是这个船的重量。真正拉动这条船的,其实是身后这些兄弟,他们对苦难的感受比我强烈。现在,对当时离开和留下的人,我都表示感激。这部戏,我一个人绝对拍不了。
晶报:上次采访你,你说你们这拨人为制作这部电影吃了那么多苦,但不代表这就是一部好片子。
陆川:对,所有的电影,工作人员都会非常苦,只是量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一部好电影,还是取决于导演和所有的主创能否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对真实的判断、对质感的判断。如果导演失去了对真实情感的判断,那么吃再多苦,拍出一部烂电影,也活该。
面对挫折,愤怒、狭隘都不可怕,我完全不会为这种情绪感到羞愧。
晶报:你曾说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是让你内心不断得到充实的一个过程,艰苦的拍摄、车祸,包括葛路明的死,这些给了你力量。我在想,经历了这些的陆川,应该已经不会再为《可可西里》落选威尼斯而受到影响,可显然你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陆川:如果你把它放在一生的长度去看,《可可西里》对我的影响我还要等两三部戏之后才能看到。它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至于像威尼斯啊,这些都是一种世俗情感。你回到城市,尤其是当它牵扯到自身的虚荣和欲望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钻出来。其实面对挫折的时候,愤怒、狭隘,都不可怕,我完全不会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感情而感觉到羞愧,有弱点多好!这证明我是一个生动的人,一个真实的人。我不会去说一些假装自己完美无缺的话。如果你真变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人,那你创作出的作品,情感也就会出问题。
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否迅速去找回终极目标,不因为欲望而改变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你真的是四大皆空,全都通透了,那你就连电影都不需要拍了。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未必在电影中显现。
晶报:一些重要的人生经历,比如非典,比如死亡,比如你去可可西里,它到底能够影响人多久?人性里最深处的东西可能就是被环境逼到那份上才会出来,你在可可西里是一种状态,等你回到城市,你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用世俗的方式世俗地生活。
陆川:我们并不是去佛学院去上了四个月的课,去修四大皆空,我们只是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去拍了四个月的戏。你要反复强化它是没必要的,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而且,你就是得回到北京,这段经历才变得有意思。因为你有了新的感受,你会综合起来比较你内心的不同感受,这才是一个挺生动的生命。
不过确实,当你回到城市,每天生活在这里,很多东西就不会像在那边那么锐利。
每个导演就算是一个盆景,你能否长得很茁壮,就在于你能否让土落在外面更广阔的土壤里。
晶报:上面那些话说得真好,看来可可西里没白去啊。
陆川:《可可西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以前我觉得等我把自己想拍的电影都拍了,还能拍什么?拍了《可可西里》,我突然通了。我想通了一个艺术家同生活和生命之间的一种关系。
晶报:什么样的关系?
陆川:每个导演就算是一个盆景吧,有的强点,长一棵小松树,有的里面也就长些烂草,但最终也都是盆景。你能否长得很茁壮,这就在于你能不能把花盆扔了,让土落在外面更广阔的土壤里,那样,你的生命力会更强。
当我们不再居高临下审视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能承认在某些人的内心中存在着比我们这些所谓导演更坚强更坚韧的东西的时候,电影有可能走上了正道。拍《可可西里》,就是完成一次发现之旅。
台前幕后
导演:陆川
美术指导:吕东
摄影指导:曹郁
主要演员:张磊饰尕玉、赵雪萤饰冷雪、亓亮饰刘栋、赵一穗饰洛桑、多布杰饰日泰
故事梗概
《可可西里》讲述的是可可西里巡山队的命运,他们从诞生到被解散,都是从一个行走的路线上展示自己的命运。从他们八个人进山,到只有两三个人活着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跟盗猎分子作战,跟环境作战,跟贫穷作战……
采访手记
用生命投注电影
采访陆川是在深夜。结束,已是次日凌晨1点半。
接下来,他还将干一个通宵,写《可可西里》宣传画册的文字稿。在他,这样的工作状态已是寻常。
采访中,我问他,可可西里那样险峻的拍摄环境里,你能在106天的拍摄期中每天都保持旺盛的激情么?他说:我的激情不止是维持了106天,而是整整2年半。从2002年筹备剧本开始直到今天。
从青海玉树到格尔木到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到海拔6200米以上的布格达坂峰,再到冷湖关机,《可可西里》剧组106天的高原拍摄旅程,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都显得单薄。陆川说,到最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带着摄制组所有成员安全走出可可西里。
这是一次创作者将生命投注电影的实践。拍摄过程丰富了创作者的内心,也反过来丰满了电影本身。
如今,因为这部《可可西里》,33岁的陆川已然开始谢顶和患上心脏病。
但他说,值了。
高丽莉 刘厚斌 深圳晶报 2004-8-12


-
相关记录
更多
- 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发现紫色新“雪莲” 2025-04-17
- 武夷山国家公园: 摸清生物“家底” 揭开物种新篇 2025-04-17
- 中美贸易战对林产品贸易影响几何? 2025-04-17
- “国土绿化·你我同行”征文活动开启 2025-04-16
- 全国古树名木保护摄影大赛作品征集启动 2025-04-15
- 木工所承担我国首个CITES公约国际合作项目 2025-04-15
 打印
打印